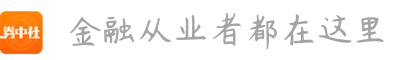想要在二战题材的电影中挖掘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吸引观众,恐怕是越来越难了。
并非是说二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已经被彻底挖掘,而是此间有太多的不可言说与不可捉摸。
《波斯语课》集中营门口装饰的的标语“依功过论处(jedem das seine)”,即是一例。
这句话源自古罗马,可理解为“每人应得到他所挣的那份”,后演变成强调社会公正的警句。
但由于多个纳粹集中营将此作为大门标语,如今变成某种禁忌,后世讳莫如深。
韭菜君并不认为《波斯语课》真如
但不可否认的是,它确实选择了一个新视角来表现纳粹集中营中的生活——一种胜利者生活。
吉尔斯的求生之路
本片中的第一条线,是吉尔斯编造假波斯语哄骗科赫以获得活着的机会。
与其他犹太人相比,他自然是胜利者。
他无意得来的《波斯神话》使他成为唯一的幸存者,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,作者在其获得此书之初便借他人之口宣告:
耶和华十诫,不可偷盗。

十诫是犹太人的生活准则,吉尔斯的生机在于背弃了十诫。
或者说,卡车带领他们的去所,是要弃绝耶和华的地方。
如果说这是一种过度的解读,那么片中纳粹士兵所巡查的破败教堂和失落的神像,岂非是纯粹的、空洞的指向?

为了保住性命,吉尔斯生活在自己所苦心经营的巨大谎言之中。
同时还要绞尽脑汁地造出一门新的语言,甚至要因他而牺牲一位真的波斯人。
如果说,《美丽人生》因其喜剧效果而使得观众忘记思考其中的逻辑,那么《波斯语课》则不得不用这种方式,来继续主人公的生命。
并不是说,主人公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择手段之人。
他的某种悲剧之处正在于不能赎罪。
他解救聋哑犹太人的计划落空,使他无法报答对方的哥哥,只能负罪在集中营里继续生活,这恰恰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。
但是,影片既没能很好地表现吉尔斯生活上的痛苦,更没有表现吉尔斯精神上的痛苦,叙事也只能流于一种奇闻。
纳粹党人的职场生活
尽管片中有多处纳粹屠杀民众的片段,但并无纳粹军官直接下达了屠杀的命令,反而更
换句话说,即杀人狂魔也有普通生活。
科赫训斥女助理无法工整地完成名册的书写;食堂里流传的,关于上司和助理的桃色新闻;两个助理为了同一位士兵的通风吃醋;科赫和指挥官互相以传言要挟对方……

不仅如此,片中还在多处展现了纳粹党人的品味。
无论是郊游时候的手风琴,还是女助理应约时的精心打扮,都让人很难与历史上的纳粹联系在一起。
如果说,有些电影以奇观性招揽观众,那么有些电影则以日常细节亲近观众。
如果不是纳粹实在给人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,恐怕会有许多观众代入其中。

科赫的不可言说
科赫的性取向在影片中有或多或少的暗示。
不管是指挥官的所谓传闻,还是他那个来路不明的德黑兰哥哥。
更可疑的是,科赫说他加入纳粹的缘由是因为被纳粹党人的外观所吸引,这些都在暧昧地指涉科赫的性身份。
原著小说中直接说明了这一点,韭菜君认为影片对此的改编是对人物复杂性的损害。
试想,一个纳粹党人本身就是被纳粹迫害的人,这样的人物难道不会更精彩?

纳粹军官为了与远在异国的兄弟见面,不惜忍受流言蜚语学习波斯语,可见它并非是泯灭人性的恶魔。
在私下里,他会写诗,会羞涩
但在这样一个制度中,这些情绪都变成了不可言说的禁忌。
恐怕他对纳粹的认同,纯粹是一种被迫的规训,从某种意义上说,他也是人质。

但作为极权齿轮的一部分,能否脱身已经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了。
当然,他或许有可以宽慰自己的地方,他只是个负责后勤的军官而已,杀人与他无关。
但站在历史面前,这样的人真的无罪吗?
如果有,他的罪又在哪里呢?
这是个已经困扰思想界半世纪之久的问题。
多余的人
不否认,片中意大利兄弟的出现和行动,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确有可能。
毕竟现实生活是无逻辑的,或者说生活的逻辑隐藏很深,但剧情片要讲逻辑。
他们俩的出现,其实并不高明,无非是为了收拾戏剧高潮留下的烂摊子。
就现实说,一座集中营很难一个波斯人都抓不到。
就剧本说,假波斯人一定要遇到真波斯人,他们的对峙会是戏剧性的高潮。
高潮容易想到,如何解决高潮才是关键所在。
影片让意大利哥哥杀掉真波斯人,这当然是个可行的办法,但始终太轻了。
人物的动机在哪里?只是因为唯有吉尔斯活着,他的弟弟才能活着吗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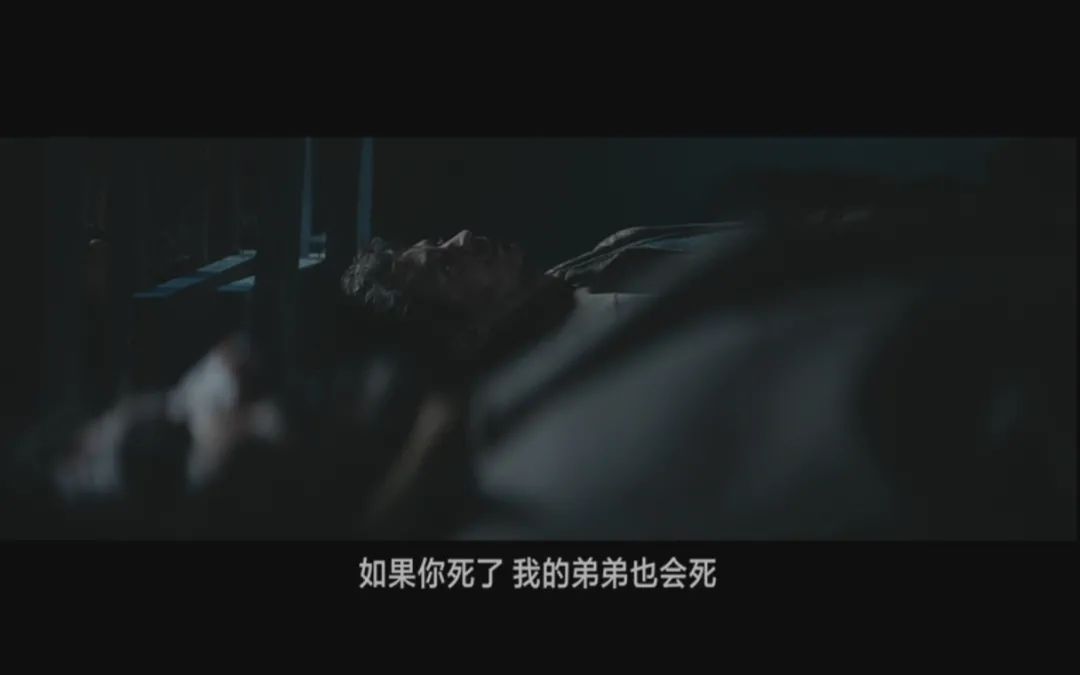
那吉尔斯帮助他弟弟的段落,能够撑得起这句话的分量吗?
自己朝不保夕的吉尔斯,能够有力量保护意大利弟弟吗?很难解释人物的动机,而高潮的分量也因缺少人物的有效行动而跌落。
我认为,以编剧的水平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,所以我称其为多余的人。
假波斯语串起的牺牲者
战争所到之处,死伤无数,往往只是一个数字。
政府积极寻找伤亡名单,其意义在于对个体的张扬,以姓名来强调生命的鲜活。
姓名是一种记忆形式,命名是一种记忆过程。
吉尔斯以姓名为基础,创造假波斯语的行为,实际上是一种再命名的行为。
是将已经湮没的个体,从壁炉的灰烬中打捞出来的行为。
更为吊诡的是,这些姓名,竟被杀害他们的纳粹军官日日念诵而不自知,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无意的讽刺。

本片为人所津津乐道也在此处,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打捞历史的“无名之辈(科赫曾形容杀戮的人)”。
影片结尾于吉尔斯对死难者姓名的背诵,两个小时的钩沉终于得到了释放。
死难者的姓名联结了记忆与未来,对战争的反思因此得以升华。
正如开头所说,本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,来自对于纳粹营生活的新表现。
在数以万计死者中活下来的人、杀人恶魔们的日常生活,光是这两个词组就已经能够吸引绝大多数人的眼球,更何况对其进行呈现。
但是,韭菜君不认为这个故事是观看二战的好方式,这并不是一件发生在远古的事情。
它依然影响着我们今日的生活。
当我们关注纳粹军官的品味和人性时,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牺牲者的沉沦和反思的停滞。
今日的世界,很难坚定地保证希特勒不会再来,战争将永远消失。
这并不是道德主义者的杞人忧天,而是我们确实没有完成痛定思痛的责任。